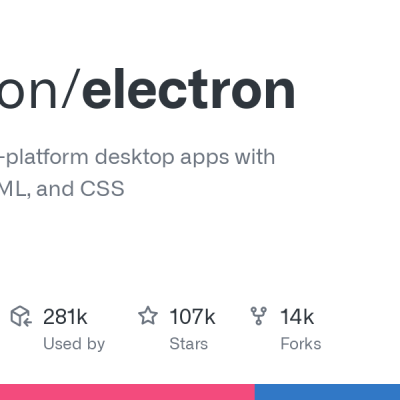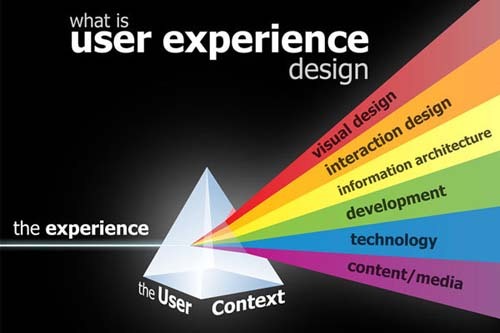GNU宣言發表 暨 自由軟體運動 30 年

Linux Story 編者按:1985年,Stallman 正式成立了自由軟體基金會(Free Software Foundation),同年發表了著名的《GNU宣言》,爾後才有了風風火火,給軟體行業帶來新氣象的「自由軟體運動」,Stallman 不僅是一名程序員,同時還是一名有教養的社會批評家,他發起的這項運動和對未來的見解,對全世界都擁有極大的影響力。時至今天2015年,FSF已經成立30年了,開源和自由軟體的理念說不上深入人心,但是大量的程序員了解和接受它,並且還在繼續著這項影響深遠的軟體行業運動。本文轉載自LCTT翻譯的《自由軟體基金會 30 年》https://linux.cn/article-6384-1.html,翻譯作者是:貓小。英文原文是:http://opensource.com/business/15/9/free-software-foundation-30-years
時光變幻
自由軟體基金會成立於1985年。讓我來描繪一下那時的計算機世界,Amiga 1000計算機已經問世,C++ 成為了那時的主宰計算機編程語言,Aldus 的 PageMaker 剛剛發布,計算機網路開始萌芽。同一年,Wham! 的 Careless Whisper 風靡各地。
30年的時間世事大變。回到1985年其時,FSF 主要關注於主要給那些計算機高手們用的自由軟體。而現在我們有軟體,有服務,社交網路和很多很多。

我首先想就 John 認為的可影響今日軟體自由的突出問題得到一些共鳴。
「我認為電腦用戶的自由面臨的巨大風險已經得到廣泛的共識,只是也許說法不同。」
「第一點是我們所謂的『微型計算機無處不在』。在這一點上自由軟體基金會算成功的,因為完全自由的操作系統可在筆記本電腦,台式電腦和伺服器上運行所有商用系統所能運行的一切。也許還有些需要修補,但它們最終將被解決。然後的挑戰是我們如何越過上億美金的市場和與我們針鋒相對的法律制度,把這些系統交付於用戶手中。」
「然而,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是那些以體積小為基本特徵的計算機設備,即便目前汽車的體積並不算小,但其內置的計算機還是很小的,此類型計算機設備,與手機,平板電腦,智能眼鏡,智能手錶等都在此討論之列。而這些計算機設備通常都以自由軟體為基礎 —— 比如說,使用 Linux 內核和一些自由軟體,例如安卓或者 GNU —— 它們的主要作用是運行專有軟體和服務支撐,由用戶無法控制的遠程伺服器替代本地計算機完成處理。這些設備服務於關鍵功能,一些對大眾通訊至關重要,還有一些貼近我們身邊,發揮實際用途,另外一些則關係到我們的人身安全,這些應該運行在自由軟體之上、完全掌控在用戶自己手中。而現如今,尚未實現。」
John 覺得危險並不僅僅是平台或形式,而是整合它們所運行的後台服務。
「我們面臨的第二大威脅是這許多設備所涉及的服務。如果我們日常工作和休閑應用都運行於我們毫無掌控的服務上的話,那麼轉而使用自由軟體則是有益無害。使用自由軟體的關鍵在於,我們可以直接看到,修改和共享代碼。這種自由相當於提供了一層保護膜,即便非技術人員也可以防止自己受制於人。而這種自由是 Facebook,Salesforce 或者 Google Docs 的使用者所感受不到的。更讓人揪心的事,有一種趨勢就是人們為了享受到某些服務,似乎適應了安裝於本地電腦的專有軟體所帶來的羈絆。瀏覽器,包含 Firefox,現如今都會自動安裝一個 DRM 插件,從而方便 Netflix 及其他一些視頻巨頭的運作。我們需要更加努力的開發去中心化的自由軟體來替換媒介分發,這樣才可以真正的讓用戶,藝術家,或者用戶藝術家有自主權,其他服務也一樣。對於 Facebook 我們有 GNU social,pump.io,Diaspora,Movim 和其它一些,對 Salesforce 我們有 CiviCRM,對 Google Docs 我們有 Etherpad,對於媒體軟體我們有 GNU MediaGoblin。但這所有的項目都需要幫助,而且許多服務我們尚沒有可替換的競爭軟體」
有趣的是,John 提到的關於找到如今常見應用軟體和服務的替換。FSF 在維護著一個「高優先順序項目」列表,設計用來彌補這些缺失。不幸的是這些項目大相徑庭,而我們又處於一個社交媒介所主宰的時代,軟體只是問題的一部分,而真正的挑戰是如何讓人們知道並使用它們。這一切都取決於 FSF 如何適應當今的計算機世界。我本人是 FSF 粉絲,我認為他們所做的努力都非常有價值,我也在經濟上支援它。他們是一個建立開放計算機環境的重要組織,但所有組織都需要成長,協調,調整,尤其是科技領域的。
我更希望了解關於 FSF 如今的作為相對於創建之初的不同。
「我們現在的聽眾相對於30年前有了很大增長,也擴大了受眾領域。現在不止是只有黑客,或者程序員和研究人員需要了解自由軟體,每一個使用計算機的人都需要,而如今幾乎人人都擁有計算機」
John 繼續提供了關於這些努力方向的一些例子。
「我們針對自由軟體運動的問題在協辦一些公眾倡議活動,早先,在這些事情上我們都會發表意見,然後酌情採取行動,但在過去的十年我們著意於制定規範和採取系列活動。我們在一些領域獲得了重大成就,比如 Design 的防缺陷數碼限制管理(DRM),這當初曾讓 iTunes 音樂下架(現在當然,Apple 已經將 DRM 應用於 Apple 音樂)。我們創建了對於自由軟體的新用戶的有吸引力和實用性的介紹資料,比如我們的用戶解放的動畫視頻和電子郵件自防衛指南。

我們還推崇尊重用戶自由的硬體。已經得到 FSF 認證的硬體提供商被要求只包含自由軟體才可顯示其認證。擴大自由軟體用戶量和自由軟體運動分為兩部分:獲取人們的關心,然後使其行動成為可能。在創始期,我們鼓勵生產商和零售商做同樣的事情,讓已經開始關注自由軟體的用戶輕鬆的買其所用,從而避免做決定前所採取的大量調查。我們已經通過認證了一種家庭 Wifi 路由器,3D 印表機,手提電腦和 USB 無線適配器,將來還會有更多。
我們收集了自由軟體目錄中能找到的所有自由軟體,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 如今我們只有 15,500 個軟體包,而我們可預知關於它們的設計和功能改進將要付出的努力 —— 但是我認為這個資源對於協助用戶找到他們需要的自由軟體有重大潛力,尤其是那些尚未使用完全 GNU/Linux 系統的用戶。面對從網路下載未知程序的潛在危險,我們絕對需要這麼一個清單。它還將成為用戶研究的機器可識別的數據資源。
我們目前為幾個特殊的軟體項目扮演著經濟資助者的角色,為它們募集資金來開發。它們中的大多數是 GNU 的組成部分(我們在持續提供著各種底層支持),但我們還資助 Replicant,一個最大限的提供用戶自由的全免費的安卓設計。
我們還幫助開發人員正確的使用免費軟體許可證,我們還在持續跟進投訴不遵循 GPL 協議的公司。我們幫助他們糾正問題而後重新部署。RMS 曾是 GPL 的先驅,但如今是我們在繼續著這項工作。
FSF 現在做的一些30年前所沒有的特別的事情,當然從最初的企划到如今有了一些變化 —— 我們的目標是創建一個用戶能在任何計算機上使用自由軟體完成一切的世界,一個絕無第二人而是用戶自己完全掌控其個人電腦的世界。」
個人崇拜
每個人心中都會關於 FSF 可能帶來的價值存有疑惑,正如 John 所提到的,我們的努力不僅涵蓋了自由軟體的開發和許可,還有認知、證實和鼓吹一種技術自由文化。
FSF 的老大是無可替代的 Richard M. Stallman,我們都稱呼他為 RMS。

RMS 擁有好奇的性格,他對於自己的主意、哲學思考和對軟體自由的道德推崇都有不可思議的展現。
他偶爾會在網上自嘲其社交上的拙劣,相對於他演講中所提之事,比如他蹩腳的旅行行頭,或者其他囧事,他對於軟體自由的見解則是堅定不移。他作為一個嚴謹的思考者對於軟體自由擁有著超凡的信仰,不僅僅是如何實現自己的構思,還有針對他領銜的活動的廣泛思考。我唯一想批評的就是他偶爾在措辭上展現的多加一個雞蛋在布丁上的貪婪,但是,考慮到他對於當今世界的重要性,我也寧願多加一個雞蛋在布丁上,也不想布丁不足以滿足每個人的需要,好吧,關於這個布丁的事情有些小題大做了。
所以說 RMS 是 FSF 的重要部分,但組織但重要性則更重要。我們有僱員,董事和其他的捐助者。我很好奇 RMS 在當今的 FSF 扮演了一個什麼角色。John 對我分享了他的觀點。
「RMS 是 FSF 總裁,但從未自 FSF 拿過一分錢報酬。他擁護自由軟體和計算機用戶自由,並且持續著滿日程的每年20多個國家的巡迴講演。他串聯社會運動,接受政要和各地區積極團體的接見,他還為 FSF 募集資金,鼓勵人們做志願者。」
「在各種忙碌間歇,他對於軟體自由運動中存在的問題做進一步思考,並且直面新的挑戰。經常這樣的舉措都會產生新的文章發布,今年初他為 Wired 寫了關於自由軟體和自由硬體設計的三篇文章,或通過與 FSF 員工交流討論從而摸索將來項目的發展。」
既然我們討論到了個人崇拜,我想針對 John 關於軟體自由運動的發展宏圖略談一二。
我記得在開源智囊團(一個聚集了各開源組織的執行者的大會)上曾有一個關於在座人員推薦任意項目許可證的用例分析,大多數重要組織都推薦了阿帕奇軟體許可(APL),而非 GNU 公眾許可證(GPL)。
這讓我記憶猶新,因為我也曾注意到許多公司看起來都選擇了 GPL 之外的其他開源許可,我很好奇是否 John 也注意到了這個 與 GPL 相斥的 APL 的發展趨勢。
「這發生了嗎?我不清楚。幾年前我為 FOSDEM 做了一個名為『版權被陷害了嗎?』的專題,它揭示了一些有據可依的許可證接納背後的問題,我也將很快為此發表一篇文章,在此列出了一些主要問題:
自由軟體協議許可的選擇並不是空中樓閣。人們選擇專有軟體許可也需要考慮各種後果,我發現人們更多是在寬鬆的許可協議(如 APL 或三句版 BSD 許可證)與專有軟體許可之間做權衡,而不是 GPL。
令人感到諷刺的是,統計軟體許可的人通常不會把他們收集數據的軟體以自由軟體發布,這意味著我們無法研究它所使用的方法或重現其統計數據。一些人現在開始發布其使用的源代碼,當然這不應該完全忽視。科學是講究方法的。
按什麼統計為一個許可證?我們真的要將 APL 之下一個發出有趣聲音的 App 和 GPLv3 下的 GNU Emacs 視同1:1嗎?如果不是,我們如何計算同等?我們只計算有功能的軟體嗎?我們確定沒有兩倍或三倍計算那些在多宿主伺服器上的應用嗎?那麼不同操作系統上之間的移植呢?

每個問題都值得推敲,但每個結論在我看來都距事實很遠。我寧願給程序員做一個調查關於為什麼他們在項目中直接選擇那些特定的軟體許可,而不是嘗試編程去探明程序的許可證的真相,然後把自己的臆想揉入這些數據中。
Copyleft 如它既往一般依舊必不可少,帶許可的軟體仍是自由軟體這怎麼說都是件好事,但它需要強有力的社會認可,不要將其納入到專有軟體。如果自由軟體主要的長期影響是讓企業能夠更有效地開發制約我們的產品的話,那麼我們對計算機用戶自由的貢獻就微乎其微了。」
直面挑戰
30年對於大多數組織都不算短,尤其是對於那些有重大目標又橫跨各行業、專業、政府和文化的組織。
當我準備結束這次訪問時,我希望自己對30歲的 FSF 現如今的發展有一個更好的理解。
「我想FSF現在處於一個非常有趣的位置,同時做為一個堅硬的磐石和一個推動潮流的推動力」
「我們有核心文檔比如 Free Software Definition 和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還有我們維護的自由和非自由軟體的許可證列表,這是創建我們當今的自由軟體世界的頂樑柱。人們非常信任這些文檔中陳述的原則,在他們的新產品和將來的實踐中正而明智的使用它們。從這個角色來說,我們為用戶的成長架設了雲梯。就好比 501(c)在法律層面為公益提供了保障,這讓85%的資金募集自個人,我們也有如斯的運營架構。」
「但我們還推進改革,我們接受別人所認為的艱巨的挑戰,我認為那說明了我們作為梯子的作用?或者我不應當用這種比喻的說法。」
John可能不善於打比方(我看起來也是),FSF 著實是善於創始大事件,並且實踐於任務的推進。而這一使命始於自由軟體應該無處不在的信仰。
「我們並不滿足於筆記本除了極少數組件外全部運行著自由軟體,也並不滿足於一個平板電腦多數運行著自由軟體,而只用專有軟體連接網路,加速視頻載入,或照相,或查詢航班,或使用Uber...好吧,我們對於這樣的發展也是欣慰的,但對於仍要取悅其它軟體卻並非我們所希望的。因為系統上安裝的任何一個專有軟體,對於用戶都既不公正,也在未來埋下了安全隱患。這些近乎自由的一切是步入自由世界的踏腳石,但這需要我們的腳步永不停歇。」
「在 FSF 早些年,我們事實上一直致力於開發一個全自由的操作系統。這現在已經被 GNU 和 Linux 和一些合作者實現了,儘管總有新的軟體要開發,總有缺陷要被處理。所以當 FSF 仍在某些領域資助自由軟體開發時,令人欣喜的是很多其他組織也在做著同樣的努力。」
面臨的挑戰中還有關鍵的一塊,John 提到,就是讓正確的人群掌控正確的硬體。
「我們目前專註於我上面提到的第一個問題的推進。對於一些特別應用我們急需一些硬體來支持自由軟體的運行。在 FSF 我們基本嘗試了我們能嘗試做的一切,我期待對我們一方面對進行中的項目提供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通過我們的尊重你的自由認證活動得以對項目進行擴展,從而開發出一些我們自己的項目。同樣的問題存在於網路服務問題。我想我們需要把它們綜合處理,因為對手機組件的完全掌控很可能會改變服務需求,而服務的分散也將更好的使手機組件化。」
「我希望人們能持續支持 FSF 的工作,尤其是當我們所面臨的這些挑戰的時候。製造提供可用的、分散而關聯的替代網路服務的硬體是昂貴而複雜的。我們將需要很多資源和有創造力的人們。但是,這在30年前,我們還只是一個圍繞在 RMS 身邊和以Copyleft 理念開發整個操作系統的社區。我過去的12年時間留給了 FSF,因為我堅信我們總會直面新的挑戰。」
寫在最後
在閱讀 John 對於我的提問所做出的回答,和在認識一些 FSF 的成員時,我有一個深切的感受,這是一個活力十足的社區。這絕非一個無聊的組織,也沒有愧對其使命,其激情和承諾一如既往的旺盛。
當然我也不總是贊同 FSF,甚至有時我覺得它所用的方法太過執拗,我將一如既往的做它死忠粉來支持它的工作。FSF 還代表了相當一部分自由軟體和全球開展的開源工作的道德水準。它代表了一種很難捨棄的世界觀,我相信它的熱情和信條幫助人們從著作權接近了著佐權(雙關語,further to the right a little closer to the left too。right/copyright 和 left/copyleft 分別代表左右和著作權/著佐權 )。
當然,RMS 有些古怪,有還有些強硬,一點敏感,但它卻是一個包容整合了技術、倫理和文化的運動的堅定的領導者。我們需要一個 RMS ,從某種程度講就如我們需要 Torvalds、Shuttleworth、Whitehurst 和 Zemlin 一樣。這些不同的人將各種遠見整合,並將技術靈活分配運用於各種不同個例,道德準則和前景發展。
所以,在完成這次採訪的時候,我想藉此機會感謝 FSF 所做出的巨大貢獻,我希望 FSF 和它的勇往直前的領導者們,Richard M. Stallman 和 John Sullivan,在未來的30年有更長足的發展。加油!